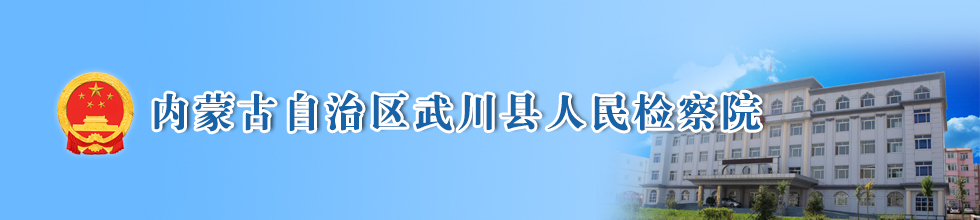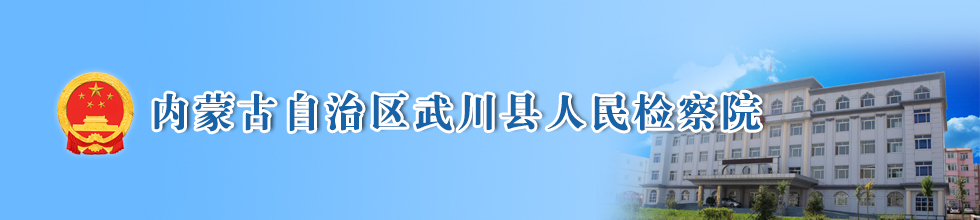公文包里带个馕,就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检察院干警翻山越岭一整天的底气。 本报记者张哲摄
车在帕米尔高原的盘山路上蜿蜒前行,窗外是苍茫的戈壁与雪山。记者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(下称“塔县”)检察院干警郑玉花:“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很远,您包里装了什么?”
“3个馕、1包干果,还有1个保温杯。”郑玉花笑了笑,掰开一半馕递过来,“要不要尝尝?虽然干了点,但挺香的。”那馕质地坚硬,嚼在嘴里带着一股质朴的麦香。郑玉花又分给同车的司机和同事,自己就着保温杯里的茶水小口吃着:“路上找不到吃饭的地方,喝点热的,胃里踏实。”
这一天,检察官要走访牧民,对公益诉讼案件开展“回头看”,同时做普法宣传,行程上百公里,海拔起伏之间,气温从近30℃跌至冰点。而郑玉花拿的公文包里,除了案卷材料、普法手册,就只剩下这些最简单也最耐放的食物——原以为这3个馕只是她路上的零食,没想到,却是她一整天的正餐。
甘肃姑娘成了“馕”检察官
大眼睛、高鼻梁,记者起初以为郑玉花是少数民族。“我是汉族人,今年是我来塔县工作的第15年,说话、气质都被‘馕’化了。”郑玉花笑着说。
郑玉花祖籍甘肃,高中时随父母搬到了新疆,大学毕业后考入塔县检察院。说起当初的选择,郑玉花至今仍觉得有些机缘巧合。在喀什时,她听说塔县是12个县市中海拔最高、最偏远的地方,但也流传着“工资高、休假时间多、工作轻松”“一年工龄算一年半”的说法。“我就是听信了这些才报考的。”说起往事,郑玉花忍不住自嘲。
刚来时,塔县条件远不如现在。从喀什到塔县,得上午九点去客运站坐大巴,一路颠簸到晚上六七点,一整天几乎全耗在路上。直到2023年,塔县机场才通航。后来,郑玉花在这里结婚生子,渐渐扎下了根、安了家。郑玉花也曾想过离开:“高原反应不是闹着玩的。”但她还是留了下来。
如今,郑玉花成了院里的办案骨干,今年是她在这儿工作的第15个年头,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。“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平原地区检察机关的同事比还有差距。有时候也想偷会儿懒、轻松一点,但案子还得一件件办,不会的就多请教,一点点学。”目前,郑玉花在塔县检察院负责民事、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业务。仅今年1月至8月,她就参与办理了公益诉讼案件37件、民事检察案件12件,完成行刑反向衔接22件,还为农民工追回欠薪72.48万元。下一步,郑玉花打算借助大数据模型,办理一批工伤保险监督案件。
这些案件背后,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。这些农民工有来自四川、甘肃等地的“塔漂”,也有不懂汉字的塔吉克族牧民。“很多人干活就靠口头约定,干完活找不到老板了,我们就得帮着追。”郑玉花说。有一次,塔吉克族老人从很远的地方骑马来到检察院,就为了送自家打的馕和酸奶表达感谢,她每次说起都忍不住眼眶发红。
“我们常说,塔县的牦牛‘喝的是冰川水,吃的是天然草,拉的是六味地黄丸’,是上天赋予帕米尔最珍贵的礼物。”郑玉花说,以前看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,觉得自己就像“山下的来客”,没那么伟大,但时间久了,她越来越被这里的冰川、牛羊和一草一木打动,渐渐把塔县当成了自己的家乡。
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高原检察公益诉讼
虽然郑玉花开玩笑说“这是一个光躺着都很累的地方”,可干起工作来,她却比谁都拼。
位于塔县的慕士塔格峰被誉为“冰山之父”,海拔7546米,冰川总面积达377平方公里,是重要的生态屏障。记者和检察官一行从海拔4200米起步,一直攀至海拔4688米的冰川边缘,郑玉花一度两眼发黑、几乎跌倒,硬是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标位置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,郑玉花就投入到工作中——摸排公益诉讼线索。
随着慕士塔格峰旅游越来越热,游客增多,安全隐患日益凸显。细心的郑玉花发现,一处观景台的木栈道出现几处裂缝,支撑结构也有些松动,且绿弓湖边没有设置有效的防护栏和警示牌,水深坡陡,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。
回到检察院后,郑玉花与同事迅速整理材料,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序,督促相关单位修复栈道、加装防护栏和警示标志,并持续跟踪整改进展。
高原上的公益诉讼,是检察官们一步步用脚丈量出来的。红其拉甫河是附近200多名牧民和护边员的“生命河”,也是提孜那甫乡的夏季牧场。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,吾甫浪沟段因化粪池检查井管网破裂污水外溢,流入红其拉甫河。
“河流被污染不仅威胁水体安全,还直接影响下游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用水,以及牲畜和野生动物的饮水安全。”郑玉花说,但办案困难接踵而至。吾甫浪沟,塔吉克语意为“死亡之谷”,这里冬季风雪狂暴,夏季洪水汹涌,要抵达该地,必须翻越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达坂(指高山顶峰),蹚过10多条冰河,穿越一片又一片乱石滩。
为了进一步取证,塔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鲁提甫拉·木太力甫带着干警由车换马,再换牦牛,一路颠簸进入吾甫浪沟。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连续蹲守3天后,他们终于成功取到水样送检、完成现场调查。“回到车上才发现,我们穿的厚鞋早已结冰,脚指头冻得发紫,完全没了知觉。”一名检察官心有余悸,“再久一点脚可能就要废了。”
事后,塔县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,并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,推动整改落实。
当然,公益诉讼也有温暖的一幕。在库科西鲁克乡,检察官发现一棵105岁的野生杏树被电线缠绕,电锯还挂在枝头,树皮也被牲畜啃得斑驳不堪。“这是我们村的‘幸福树’,但不知道该怎么保护。”村民古丽比比说。
“看到电锯挂在树上,我心里一紧。”检察官吐尔荪江·斯麦提说。他们立即协助村民清理周围柴火、排除隐患,并召开听证会,依法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。
检察官助理古力那孜·亚力坤说:“围绕古树保护,我们依照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,对县域内8棵挂牌古树全部‘问诊’了一遍,并将线索立案调查。跟着团队深入乡村勘查古树,亲眼看到法律条文转化为实际行动后,我更加坚定了用法治守护高原生态的决心。”
“检察官来了,古树又活过来了。”当地农牧民这样说。
他乡作故乡
“原本只打算待一阵子,没想到一晃眼好像要待上一辈子。”时间久了,郑玉花学会了骑马,跟着牧民季节转场,习惯了牧民家的毡房,甚至一日三餐只有馕和奶茶。“我们出去办案也一样,带个馕、背壶水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当事人住得分散,方圆百里可能只有一两户,经常得靠村干部带路才找得到。就像这次去冰川,我包里就塞了3个馕。这儿地方大、路远,意外情况多,有备无患。”郑玉花说。
他乡作故乡,这是塔县检察人的真实写照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喀什分院副检察长张宏南感叹:“塔县检察院人数较少,办案水平与平原地区检察院相比偏弱,喀什检察分院每年都由副检察长带队,蹲点指导一段时间,集中办理一批‘四大检察’案件,提升基层办案能力。”为了帮助提升干警业务能力与办案水平,喀什检察分院自今年1月起,选派骨干干警来塔县支援业务工作。每批同志支援周期为6个月。首批4位同志刚完成任务不久,目前第二批力量也已到岗,接续开展相关工作。
“虽然塔县属于喀什地区,但与市区在海拔、气候上都有很大差别,有些从喀什第一次来塔县的人也不适应,只能氧气罐不离手。”喀什检察分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宋烁说。
自2020年以来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持续开展“雪山冰川保护”检察公益诉讼专项行动。塔县检察院深入高原摸排线索,针对冰川附近垃圾填埋污染等问题制发检察建议,消除生态威胁;联合河长办构建三级河湖长体系,68名河长常态化巡河,2025年清理违规建筑6处,整治非法采砂点,保障了冰川融水水源安全。
在喀什检察分院指导下,塔县检察院还与阿克陶县检察院组成联合调研组,深入喀拉库勒湖、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实地勘查,采集数据、排查风险,并签署跨区域协作协议。
除了本地的“传帮带”,“外部输血”也同样重要。2023年底,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成立“援塔工作组”,赴塔县开展业务援建。初来乍到,工作组中的3名成员不同程度出现头痛、头晕、耳鸣、乏力、难以入眠等症状。“缺氧、干燥,大家每晚都会被渴醒,早上起床还会流鼻血。”工作组成员说。当地检察干警克服高寒高反和人员紧缺等困难,毅然选择了坚守、付出和奋斗。有的干部和爱人、孩子长期两地分居,半年见不到一次面;有的人驻村期间遭遇大雪封山……
“我们深深为他们无怨无悔扎根边疆的精神感动,也希望尽一份绵薄之力。”工作组成员由衷地说。他们以支持起诉、虚假诉讼监督等为重点,从办案理念、办案模式、办案思路、办案方式等全方位相互交流学习、共促进步。
一切为了把人留下
塔县检察院,这个仅有十几人的小检察院,也让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6期巡讲支教团深受触动。2024年7月,这支专攻公益诉讼团队的到来,被塔县检察院干警称作“及时雨”——不只是知识的传递,更如荒漠中的清泉,“解了渴,也答了惑”。
巡讲团很快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沉默与艰难:塔县地广人稀,取证困难、技术有限,案件推进步履维艰。于是,一个“公益诉讼业务交流群”悄然建起。屏幕那端,是“带不走的老师”;屏幕这边,是再也断不开的牵挂。
“这一站,是我们全程走过的海拔最高的土地之一。我的血氧一度跌到80,只能靠着鼻吸持续供氧。”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助理宁中平说,“从维稳到发展,从民族团结到文化交融,每一项工作,靠的都是心血。条件再苦、人再少,塔县检察院同事们的眼里也有光。无论从哪里开始聊,最终总能回到公益诉讼——那是他们的信念,也是他们的乡愁。”
有检察官笑着调侃,大家多少也染上了一点“高原病”,但这些却没有成为他们离开的理由。塔县检察院党组书记、副检察长凡艳峰说:“我们所做的一切,说到底就是为了把人留下。不是为了留下谁,而是让每一个选择这里的人都能被看见、被支持、被珍惜。”
8月的塔县,晚上10点天才开始黑,转瞬却已寒意袭人。采访接近尾声,记者躲进院里一座温室棚,西红柿正红,西瓜渐熟,更远的棚中还有几只大鹅在悠闲地踱步——像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在苍茫天地间顽强地绽放生命。